2017年5月1日起實施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常見犯罪的量刑指導意見(二)》(以下簡稱《量刑指導意見》)規定:“對于醉酒駕駛機動車的被告人……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予定罪處罰。犯罪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的,可以免予刑事處罰。”這一規定為醉駕行為原則性地保留了出罪空間,已經從實然層面終結了關于醉駕行為是否一律應成立犯罪的爭論。
在我國刑法中,正當化事由承擔著行為符合犯罪構成四要件之后的出罪(阻卻入罪)功能。目前,我國刑法明文規定的正當化事由有兩個,分別是第20條的正當防衛與第21條的緊急避險。事實上,近年來在司法實踐中,已然存在司法機關將醉駕送他人就醫的行為認定為緊急避險,從而予以出罪化處理的先例。由此可見,在醉駕行為成立緊急避險的場合,由于行為的避險對象并不限于具體現實的個體主體,避險結果也不要求一定出現現實性的物質損害。所以,在醉駕案件的處理中,存在適用緊急避險制度進行出罪的空間。至于醉駕行為在何種情況下才能成立緊急避險,則需結合緊急避險的正當性依據與成立條件進行具體探討。
一方面,緊急避險的正當性依據就是其承擔出罪功能的原因所在,所以其成立條件的立法設置與司法判斷都要基于此依據而展開。事實上,依據避險行為指向的對象不同,緊急避險可以分為攻擊性緊急避險與防御性緊急避險,前者指向無辜第三方,后者則指向危險源本身,二者的正當性依據是不同的。前者的正當性依據在于無辜第三人作為社會共同體的組成部分之一所負有的社會團結(容忍)義務;后者則在于基于法益衡量思維而產生的優越利益原理,即避險行為所保護的法益大于其可能犧牲掉的利益。就可以構成緊急避險的醉駕行為而言,逃避或擺脫危險的功能屬性才是其之所以為行為人選中的原因所在,而針對危險源本身的抑制或消滅并非其可以達成的效果。再者,采用醉駕行為作為避險行為,會在行為過程中通過抽象危險的方式為道路交通運輸領域內的公共安全這一“無辜的”集體法益帶來不利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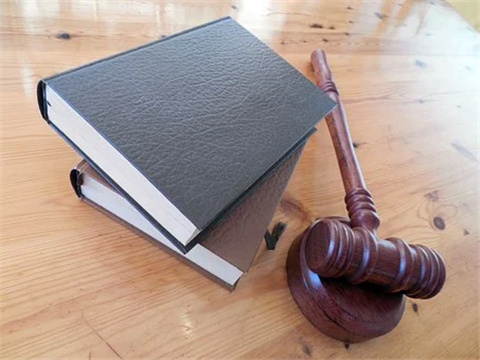
另一方面,醉駕行為只有在符合緊急避險的各項成立條件之時才能成立緊急避險,從而具備出罪的正當性。對此,以醉駕送緊急病患就醫這一情況為例具體展開。
第一,就避險對象來講,其應為醉駕送醫所經道路范圍內不特定或多數人的生命健康、財產權益的安全。
第二,就避險意圖而言,醉駕行為人必須對他人病情的緊急情況有一個基本認識,并且還應認識到對這種危險只能通過自己的醉駕行為將其送醫的方法來予以排除,同時還應以挽救病患的生命健康為目的。
第三,就避險起因而言,病患因緊急病情而導致的自身生命健康所面臨的危險必須是客觀存在的,不能是被醉駕行為人假想存在的。
第四,就避險時間而言,其應處于危險正在發生或迫在眉睫之時,即病患正在發病且癥狀明顯之時。此時,病患的生命健康權正面臨著疾病所帶來的緊迫且直接的危險,危在旦夕。在病患疾病未發作之時送其體檢或病患發病后癥狀緩和因而已無緊迫危險時送其就診的醉駕行為,會因避險不適時而不構成緊急避險。
第五,就避險限制而言,成立緊急避險的醉駕行為只有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才可以實施。具體而言,病患通過其他方式也可以得到及時救助時,就不能通過醉駕送醫的方式予以排除危險,否則可能導致相關醉駕人員以送病患就醫為借口濫用緊急避險規則來逃避法律制裁。
第六,就避險禁止而言,此條件主要針對以下這一特殊情況,即強調職務或業務上負有特殊職責的人因履職而面對危險時,為保護自己而不履行排除危險職責或義務的瀆職行為不能成立緊急避險,因而不能出罪。由于醉駕型危險駕駛罪在分則罪名體系中不屬于瀆職犯罪類別,因此其不適用于通過醉駕行為送病患就醫而成立緊急避險的場合。
第七,就避險限度而言,醉駕行為不能超過必要限度,造成不應有的損害。雖然攻擊性緊急避險的正當化依據在于上述社會團結(容忍)義務,但是,在避險限度判斷這一技術性問題上,仍需借助法益衡量原理來使界定社會團結義務范圍的任務更具備可操作性。具體而言,雖然道路內的不特定或多數人的生命健康權看似大于病患的生命健康權,但是,前者在醉駕行為發生的場域只是經受了法律擬制的抽象危險,其緊迫程度不可與正在嚴重發病的病患之生命健康權所受的具體現實的危險相提并論。因此,在一般情況下,醉駕所經過道路范圍內的公眾只對這種法律擬制的抽象危險具有社會團結(容忍)義務,但當醉駕行為突破了必要限度,造成了無辜路人出現不應有的傷亡情況時,則構成避險過當,視情節予以減輕或免除處罰。

綜上,當醉駕送病患就醫行為符合上述條件時,就可因成立緊急避險而予以出罪。而這一分析過程同樣適用于醉駕送自己就醫或醉駕躲避其他危險等可能成立緊急避險的其他情況。因此,醉駕行為所能構成的緊急避險只能是攻擊型緊急避險,就其表現形式而言,可以是醉駕送嚴重病患就醫、醉駕逃離緊迫的危險;等等。那么,特定醉駕行為成立緊急避險的正當性,是否在于前述集體法益的主體——社會具有對避險醉駕行為的容忍義務呢?
在醉駕案件的處理中,存在適用緊急避險制度進行出罪的空間。至于醉駕行為在何種情況下才能成立緊急避險,則需結合緊急避險的正當性依據與成立條件進行具體探討。緊急避險的正當性依據就是其承擔出罪功能的原因所在,所以其成立條件的立法設置與司法判斷都要基于此依據而展開。醉駕行為只有在符合緊急避險的各項成立條件之時才能成立緊急避險,從而具備出罪的正當性。
對這一問題,需要聯系集體法益的相關理論知識進行深入探討。現代刑法理論中的法益有個人法益與集體法益之分。前者側重于保護個人自由,而后者則強調維護秩序。由于傳統上以個人法益保護為中心的刑法,無法有效回應現代社會的各種風險和挑戰,因而集體法益的保護在現代刑法中呈現擴張趨勢。然而,過度擴張集體法益的內容勢必導致對公民個人自由空間的不斷侵蝕,有悖于現代法治國家尊重與保護人權的價值理念。因此,對于集體法益而言,只有其在解釋論上可以被還原為個人法益之時,才值得為刑法所保護。而醉駕型危險駕駛罪所保護的法益——道路交通運輸領域的公共安全,可以被還原成構成社會這一規范共同體之全體公民在此領域內的生命健康與重大公私財產安全。那么,當道路交通運輸領域內的全體公民基于社會團結義務有必要容忍特定醉駕行為對自身生命健康、重大公私財產安全造成的抽象危險時,特定醉駕行為則構成緊急避險這一刑法中的正當化事由之一,從而不成立犯罪。當然,公民的團結與容忍義務不是無限的,對于其合理程度的界定則需結合緊急避險的各成立條件,尤其是限度條件,并參考優越利益或法益衡量原理,進行具體分析。
| 醉駕丈夫深夜送病重妻子就醫被查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