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六十條 內容
第二百六十條 虐待家庭成員,情節惡劣的,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犯前款罪,致使被害人重傷、死亡的,處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款罪,告訴的才處理,但被害人沒有能力告訴,或者因受到強制、威嚇無法告訴的除外。
釋義闡明
本條是關于虐待罪的處刑規定。
根據本條的規定,虐待罪是指虐待家庭成員,情節惡劣的行為。這里聽說的“虐待”,具體是指經常以打罵、凍餓、捆綁、強迫超體力勞動、限制自由、凌辱人格等各種方法,從肉體、精神上迫害、折磨、摧殘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員的行為。虐待行為區別于偶爾打罵或者偶爾的體 罰行為的明顯特點是:虐待行為往往是經常甚至一貫進行的,具有相對連續性。這里所說的“家庭成員”,是指在同一家庭中共同生活的成員 。非家庭成員間的虐待行為,不構成本罪。根據本款的規定,虐待家庭成員必須是情節惡劣的才能構成犯罪。這里所說的“情節惡劣”,是本 罪的罪與非罪的重要界限,具體是指虐待的動機卑鄙、手段兇殘的;虐待年老、年幼、病殘的家庭成員的;或者長期虐待家庭成員屢教不改的 ,等等。依照本條第一款的規定,虐待家庭成員,情節惡劣的,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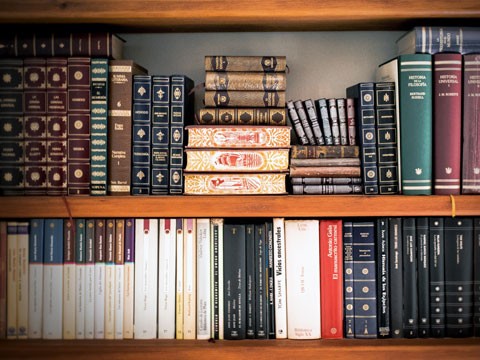 故意傷害罪或者故意殺人罪,應依照本法關于故意傷害罪或者故意殺人罪的規定定罪處罰。
故意傷害罪或者故意殺人罪,應依照本法關于故意傷害罪或者故意殺人罪的規定定罪處罰。
 假釋時,應當充分聽取被害人意見,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作出合情、合理的處理。對法律規定可以調解、和解的案件,應當在當事人雙方自愿的基礎上進行調解、和解。 4.對未成年人、老年人、殘疾人、孕婦、哺乳期婦女、重病患者特殊保護。辦理家庭暴力犯罪案 件,應當根據法律規定和案件情況,通過代為告訴、法律援助等措施,加大對未成年人、老年人、殘疾人、孕婦、哺乳期婦女、重病患者的司法保護力度,切實保障他們的合法權益。 二、案件受理
假釋時,應當充分聽取被害人意見,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作出合情、合理的處理。對法律規定可以調解、和解的案件,應當在當事人雙方自愿的基礎上進行調解、和解。 4.對未成年人、老年人、殘疾人、孕婦、哺乳期婦女、重病患者特殊保護。辦理家庭暴力犯罪案 件,應當根據法律規定和案件情況,通過代為告訴、法律援助等措施,加大對未成年人、老年人、殘疾人、孕婦、哺乳期婦女、重病患者的司法保護力度,切實保障他們的合法權益。 二、案件受理
 取保候審的,為了確保被害人及其子女和特定親屬的安全,可以依照刑事訴訟法第六十九條第二款的規定,責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得再次實施家庭暴力;不得侵擾被害人的生活、工作、學習;不得進行酗酒、賭博等活動;經被害人申請且有必要的,責令不得接近被害人及其未成年子女。
取保候審的,為了確保被害人及其子女和特定親屬的安全,可以依照刑事訴訟法第六十九條第二款的規定,責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得再次實施家庭暴力;不得侵擾被害人的生活、工作、學習;不得進行酗酒、賭博等活動;經被害人申請且有必要的,責令不得接近被害人及其未成年子女。
14.加強自訴案件舉證指導。家庭暴力犯罪案件具有案發周期較長、證據難以保存,被害人處于相對弱勢、舉證能力有限,相關事實難以認定等特點。有些特點在自訴案件中表現得更為突出。因此,人民法院在審理家庭暴力自訴案件時,對于因當事人舉證能力不足等原因,難以達到法律規定的證據要求的,應當及時對當事人進行舉證指導,告知需要收集的證據及收集證據的方法。對于因客觀原因不能取得的證據,當事人申請人民法院調取的,人民法院應當認真審查,認為確有必要的,應當調取。
15.加大對被害人的法律援助力度。人民檢察院自收到移送審查起訴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內,人民法院自受理案件之日起三日內,應當告知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親屬有權委托訴訟代理人,如果經濟困難,可以向法律援助機構申請法律援助;對于被害人是未成年人、老年人、重病患者或者殘疾人等,因經濟困難沒有委托訴訟代理人的,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應當幫助其申請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機構應當依法為符合條件的被害人提供法律援助,指派熟悉反家庭暴力法律法規的律師辦理案件。
三、定罪處罰
16.依法準確定罪處罰。對故意殺人、故意傷害、強奸、猥褻兒童、非法拘禁、侮辱、暴力干涉婚姻自由、虐待、遺棄等侵害公民人身權利的家庭暴力犯罪,應當根據犯罪的事實、犯罪的性質、情節和對社會的危害程度,嚴格依照刑法的有關規定判處。對于同一行為同時觸犯多個罪名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
17.依法懲處虐待犯罪。采取毆打、凍餓、強迫過度勞動、限制人身自由、恐嚇、侮辱、謾罵等手段,對家庭成員的身體和精神進行摧殘、折磨,是實踐中較為多發的虐待性質的家庭暴力。根據司法實踐,具有虐待持續時間較長、次數較多;虐待手段殘忍;虐待造成被害人輕微傷或者患較嚴重疾病;對未成年人、老年人、殘疾人、孕婦、哺乳期婦女、重病患者實施較為嚴重的虐待行為等情形,屬于刑法第二百六十條第一款規定的虐待“情節惡劣”,應當依法以虐待罪定罪處罰。
準確區分虐待犯罪致人重傷、死亡與故意傷害、故意殺人犯罪致人重傷、死亡的界限,要根據被告人的主觀故意、所實施的暴力手段與方式、是否立即或者直接造成被害人傷亡后果等進行綜合判斷。對于被告人主觀上不具有侵害被害人健康或者剝奪被害人生命的故意,而是出于追求被害人肉體和精神上的痛苦,長期或者多次實施虐待行為,逐漸造成被害人身體損害,過失導致被害人重傷或者死亡的;或者因虐待致使被害人不堪忍受而自殘、自殺,導致重傷或者死亡的,屬于刑法第二百六十條第二款規定的虐待“致使被害人重傷、死亡”,應當以虐待罪定罪處罰。對于被告人雖然實施家庭暴力呈現出經常性、持續性、反復性的特點,但其主觀上具有希望或者放任被害人重傷或者死亡的故意,持兇器實施暴力,暴力手段殘忍,暴力程度較強,直接或者立即造成被害人重傷或者死亡的,應當以故意傷害罪或者故意殺人罪定罪處罰。
 緩刑的犯罪分子,為了確保被害人及其子女和特定親屬的人身安全,可以依照刑法第三十八條第二款、第七十二條第二款的規定,同時禁止犯罪分子再次實施家庭暴力,侵擾被害人的生活、工作、學習,進行酗酒、賭博等活動;經被害人申請且有必要的,禁止接近被害人及其未成年子女。
緩刑的犯罪分子,為了確保被害人及其子女和特定親屬的人身安全,可以依照刑法第三十八條第二款、第七十二條第二款的規定,同時禁止犯罪分子再次實施家庭暴力,侵擾被害人的生活、工作、學習,進行酗酒、賭博等活動;經被害人申請且有必要的,禁止接近被害人及其未成年子女。
22.告知申請撤銷施暴人的監護資格。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對于監護人實施家庭暴力,嚴重侵害被監護人合法權益的,在必要時可以告知被監護人及其他有監護資格的人員、單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請,要求撤銷監護人資格,依法另行指定監護人。
23.充分運用人身安全保護措施。人民法院為了保護被害人的人身安全,避免其再次受到家庭暴力的侵害,可以根據申請,依照民事訴訟法等法律的相關規定,作出禁止施暴人再次實施家庭暴力、禁止接近被害人、遷出被害人的住所等內容的裁定。對于施暴人違反裁定的行為,如對被害人進行威脅、恐嚇、毆打、傷害、殺害,或者未經被害人同意拒不遷出住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情節輕重予以罰款、拘留;構成犯罪的,應當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24.充分運用社區矯正措施。社區矯正機構對因實施家庭暴力構成犯罪被判處管制、宣告緩刑、假釋或者暫予監外執行的犯罪分子,應當依法開展家庭暴力行為矯治,通過制定有針對性的監管、教育和幫助措施,矯正犯罪分子的施暴心理和行為惡習。 25.加強反家庭暴力宣傳教育。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司法行政機關應當結合本部門工作職責,通過以案說法、社區普法、針對重點對象法制教育等多種形式,開展反家庭暴力宣傳教育活動,有效預防家庭暴力,促進平等、和睦、文明的家庭關系,維護社會和諧、穩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民政部《關于依法處理監護人侵害未成年人權益行為若干問題的意見》(2015年1月1日施行 法發〔2014〕24號)
一、一般規定
1.本意見所稱監護侵害行為,是指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以下簡稱監護人)性侵害、出賣、遺棄、虐待、暴力傷害未成年人,教唆、利用未成年人實施違法犯罪行為,脅迫、誘騙、利用未成年人乞討,以及不履行監護職責嚴重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等行為。
2.處理監護侵害行為,應當遵循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則,充分考慮未成年人身心特點和人格尊嚴,給予未成年人特殊、優先保護。
3.對于監護侵害行為,任何組織和個人都有權勸阻、制止或者舉報。
二、報告和處置
14.監護侵害行為可能構成虐待罪的,公安機關應當告知未成年人及其近親屬有權告訴或者代為告訴,并通報所在地同級人民檢察院。
未成年人及其近親屬沒有告訴的,由人民檢察院起訴。
1第二百六十條 證據規格
虐待罪:
(一)關于本罪主體的證據
本罪的主體為一般主體,即年滿十六周歲、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自然人。
(二)關于本罪主觀方面的證據
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辯解。證實
(1)實施危害行為的目的,是否具有故意傷害或其他侵害的目的;(2)是否意識到危害行為的危險性以及可能會傷害他人的后果;(3)在實施危害行為前后和過程中的言行及其所產生的后果。
2.被害人陳述。證實:
(1)其與行為人是否認識、平時關系,是否與行為人有過節等;(2)行為人在實施危害行為前后和行為時的言行及其所產生的后果;(3)行為人是否曾有故意傷害或其他侵害的意思表示和舉動。
3.證人證言:
(1)現場圍觀群眾、目擊證人證言,證實其所看到(聽到)的行為人和被害人的言行,實施危害行為的過程和現場情況;(2)知情人證言,證實行為人與被害人否有矛盾,行為人是否曾有故意傷害或其他侵害的意思表示和舉動。
4.書信、日記等書證。證實行為人與被人是否有矛盾,以及行為人是否具有故意傷害或其他侵害的意思表示通過上述證據并結合客觀方面的證據,證明行為人對其所實施的危害行為及其危險性,以及致人重傷的危害結果發生的心理態度是疏忽大意的過失或過于自信的過失。
(三)關于本罪客觀方面的證據
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辯解。證實:
(1)實施危害行為的時間、地點;
(2)實施危害行為的方式,手段;
(3)作案工具的來源、數量、特征、下落;
(4)侵害部位及打擊次數、被害人當場的受傷情況(5)實施危害行為的具體過程
(6)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害人的身體征,包括面部特征、身高、體態,以及當時的衣著情況等詳細特征(7)犯罪現場是否有圍觀群眾或者其他見證人;
(8)犯罪后的表現情況,如是否有積極搶救被害人的行為,是否賠償了被害人的經濟損失2.被害人陳述。證實被侵害過程等情況
3.證人證言。證實其所了解的侵害過程和現場情況等,包括(1)目擊證人證言,證實
①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害人的關系;
②案發時間、地點、原因
③雙方的情況,包括行為人和被害人的面部特征、身高、體態、衣著等④在案發現場所看見、聽到的一切與案件事實相關的情況(2)抓獲人、扭送人證言,證實
①如何獲知犯罪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情況;
②抓獲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時間、地點、過程
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有投案、坦白、立功情節;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抓獲時的身體特征、衣著情況的描述⑤若有多名抓獲者,證言中的不一致之處應有合理解釋(3)現場發現人證言,證實其何時、何地、如何發現犯罪現場以及犯罪現場的有關情況(4)被害人親友對被害人被害前后的身健康狀況如勞動能力、智力狀況、后遺癥等的證言;(5)其他知情人的證言。
4.物證、書證:
(1)作案工具,如刀槍、毒藥、繩索等
(2)現場遺留痕跡,如指紋、腳印、壓痕、彈痕、齒痕等;(3)現場遺留的血衣、血跡、毛發等;
(4)書信、日記等,證實行為人實施殺害行為的時間、地點及經過等情況;(5)電信部門提供的(固定、移動)電話通話記錄、短信息記錄;(6)病歷、搶救記錄,死亡證明;
(7)民事賠償調解協議(筆錄)、欠條等,佐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認其犯罪行為及后果。
5.鑒定意見:
(1)法醫鑒定意見,證實兇器種類、打擊部位、被害人傷情等;(2)痕跡鑒定意見,對上述指紋、腳印、壓痕、彈痕、齒痕等進行鑒定,證實是否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被害人遺留的;(3)文檢鑒定意見,證實有關書證上的字跡、印鑒是否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被害人的;(4)血型、DNA鑒定意見,證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被害人身體、衣物及現場遺留的血衣、血跡、毛發等是否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被害人的;(5)傷殘鑒定意見。
6.勘驗、檢查筆錄:
(1)現場勘查筆錄、照片,證實案發現場等;
(2)人身檢查筆錄及照片,證實被害人行為人身體特征、傷情等。
7.視聽資料。包括錄音、錄像等能夠證明案件有關情況的資料。
8.其他證明材料
(1)被害人、目擊證人辨認犯罪嫌疑人或物證的筆錄;(2)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害人、證人指認現場筆錄;(3)搜查筆錄、扣押物品清單及照片,證實查獲的作案工具及調取的相關物證:
(4)偵查實驗筆錄、錄像;
(5)報案登記、立案決定書及破案經過等書證,證實案件來源、偵破經過以及犯罪嫌疑人是否有自首情節等通過上述證據,證明行為人實施了過失造成他人重傷的行為。
實踐中,應注意:不作為引起他人重傷的行為的主觀內容有的是故意,有的是過失。要注意收集和運用有助于證實主觀內容的相應證據。
(四)關于本罪客體的證據
本罪的客體,是他人的身體健康的權利。主要通過上述主、客觀方面的證據予以證明。
實務指南
1高銘暄、李彥峰:“因受到強制、威嚇無法告訴”的虐待案件應當一律予以公訴處理##只有最大程度地實現虐待罪被害人追訴權利的保障、虐待罪被害人追訴意愿的尊重以及國家特定社會秩序的維護三者關系的平衡,才能合理劃定虐待罪“告訴才處理”的適用范圍:通過對“沒有能力告訴”的擴大解釋,將虐待罪案件最大程度地納入公訴范圍,以實現虐待罪被害人追訴權利的保障;借助法律規范賦予的被害人自訴或公訴的程序選擇權,以實現虐待罪被害人追訴意愿的尊重;利用對“輕微家庭暴力犯罪案件”范圍的合理界定,以實現國家特定社會秩序的維護。“因受到強制、威嚇無法告訴”除外規定的立法變化反映出立法者突出被害人合法權益保護與特定社會秩序維護的價值傾向,對于“因受到強制、威嚇無法告訴”的虐待案件應當一律予以公訴處理。
 死刑。原判對蔡世祥判處有期徒刑七年的量刑不當,應予改判。抗訴機關提出的第二項抗訴理由成立,予以支持。
死刑。原判對蔡世祥判處有期徒刑七年的量刑不當,應予改判。抗訴機關提出的第二項抗訴理由成立,予以支持。
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九條第(二)項、《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條第二款之規定,判決如下:
1.撤銷義縣人民法院的刑事判決。
2.原審被告人蔡世祥犯故意傷害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二年。
二、主要問題
1.虐待罪與故意傷害罪之間是否存在法條競合關系?
2.虐待中又實施故意傷害行為的,如何定罪?
三、裁判理由
(一)虐待罪與故意傷害罪之間不存在法條競合關系法條競合是指一個犯罪行為因為法律的錯綜規定,而同時符合了數個在構成要件上存在著交叉關系或包容關系的刑法分則條文,但只能適用其中一個條文而排斥其他條文適用的情形。刑法分則條文之間發生競合關系,主要是因法律規定的各罪名的構成要件上有交叉或者包容關系,僅僅因為行為人實施的具體犯罪行為而使數個法條對行為均具符合性,而該數法條之間并無必然包容或交叉關系的,不是法條競合,而是想象競合犯。
虐待罪與故意傷害罪是否存在法條競合關系是本案審理中的焦點問題,一審法院對此給予了肯定,而二審法院則否定了一審認定結論。我們認為,如上所述,判斷虐待罪與故意傷害罪是否存在法條競合關系的關鍵在于兩罪的構成要件是否存在交叉或包容關系,根據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條和第二百六十條的規定,虐待罪與故意傷害罪的犯罪構成要件完全不同,并不存在構成要件上的交叉或包容關系:一是犯罪主體不同。虐待罪的犯罪主體為特殊主體,只有行為人與被害人具有家庭成員關系時才構成;故意傷害罪的犯罪主體為一般主體。二是故意內容不同。虐待罪的主觀故意是使被虐待者肉體上、精神上受摧殘、折磨,行為人并不想直接造成被害人傷害、死亡的結果,被害人所以致傷、致死是由于長期虐待的結果;故意傷害罪的行為人則積極追求或放任傷害后果的發生。三是侵犯客體不同。虐待罪侵犯的是復雜客體,即家庭成員在家庭生活中的平等權利和被害人的人身權利;故意傷害罪侵犯的是單一客體,即他人的身體健康權。四是行為特點不同。虐待罪中的虐待行為具有連續性、經常性和一貫性,這是引起被害人致傷、致死的原因,一次的虐待行為不足以構成虐待罪,更不足以造成被害人傷亡結果的發生;而故意傷害罪對被害人身體的傷害一般情況下為一次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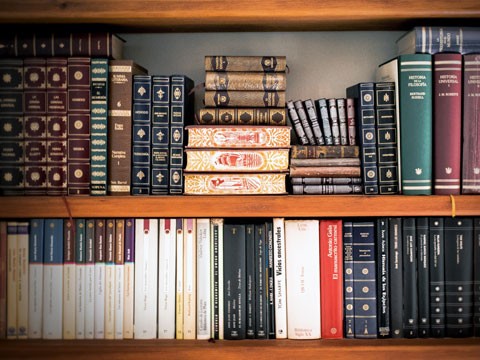
最高法典型案例 朱朝春虐待案
來源:最高人民法院發布涉家庭暴力犯罪典型案例
(2015年3月4日)
朱朝春虐待案
(一)基本案情
1998年9月,被告人朱朝春與被害人劉祎(女,歿年31歲)結婚。2007年11月,二人協議離婚,但仍以夫妻名義共同生活。2006年至案發前,朱朝春經常因感情問題及家庭瑣事毆打劉祎,致劉祎多次受傷。2011年7月11日,朱朝春又因女兒的教育問題及懷疑女兒非自己親生等與劉祎發生爭執。朱朝春持皮帶抽打劉祎,致使劉祎持刀自殺。朱朝春隨即將劉祎送醫院搶救。經鑒定,劉祎體表多處挫傷,因被銳器刺中左胸部致心臟破裂大失血,經搶救無效死亡。當日,朱朝春投案自首。
(二)裁判結果
湖北省武漢市漢陽區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朱朝春經常性、持續性地采用毆打等手段損害家庭成員身心健康,致使被害人劉祎不堪忍受身體上和精神上的摧殘而自殺身亡,其行為已構成虐待罪。朱朝春自動投案,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構成自首,可以從輕處罰。依照刑法有關規定,以虐待罪判處被告人朱朝春有期徒刑五年。宣判后,朱朝春提出上訴。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經依法審理,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三)典型意義
本案是一起虐待共同生活的前配偶致被害人自殺身亡的典型案例。司法實踐中,家庭暴力犯罪不僅發生在家庭成員之間,在具有監護、扶養、寄養、同居等關系的人員之間也經常發生。為了更好地保護兒童、老人和婦女等弱勢群體的權利,促進家庭和諧,維護社會穩定,《關于依法辦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見》將具有監護、扶養、寄養、同居等關系的人員界定為家庭暴力犯罪的主體范圍。本案被告人朱朝春雖與被害人劉祎離婚,二人仍以夫妻名義共同生活,朱朝春經常性、持續性地實施虐待行為,致使劉祎不堪忍受而自殺身亡,屬于虐待“致使被害人死亡”的加重處罰情節,應依法予以重判。
最高法典型案例 王玉貴故意傷害、虐待案
來源: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五起依法懲治侵犯兒童權益犯罪典型案例(2014年5月28日)王玉貴故意傷害、虐待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王玉貴系被害人張某(女,出生于2001年4月9日)的繼母。2009年5月19日晚,王玉貴在家中用筷子將張某咽部捅傷,致張某輕傷;另查明,被告人王玉貴自2005年開始與張某共同生活,其間經常趁張某生父張建志不在家時,多次對張某實施打罵、用鉛筆尖扎等虐待行為。2005年春季的一天,王玉貴用吹風機將張某的頭皮和耳朵燙傷。2008年12月的一天,王玉貴在家中將張某的嘴唇撕裂,次日上午張某至醫院縫了三針并留下疤痕。
(二)裁判結果
河北省鹽山縣人民檢察院以被告人王玉貴犯故意傷害罪,向鹽山縣人民法院提起公訴。在審理過程中,自訴人張某及其法定代理人、張某的生母張美麗以被告人王玉貴犯虐待罪,向鹽山縣人民法院提起告訴。鹽山縣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人王玉貴故意用筷子戳刺繼女張某的咽喉,造成張某輕傷,其行為已構成故意傷害罪;王玉貴在與張某共同生活期間,對張某實施毆打、用鉛筆尖扎、用吹風機燙頭皮、撕嘴唇等虐待行為,情節惡劣,其行為已構成虐待罪,應依法懲處。依照刑法規定,判決被告人王玉貴犯故意傷害罪,判處其有期徒刑二年;犯虐待罪,判處其有期徒刑一年,決定執行有期徒刑三年。
宣判后,被告人王玉貴提出上訴。河北省滄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經依法審理,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三)典型意義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繼母對未成年子女實施家庭暴力構成犯罪的案件,其中反映出兩點尤其具有參考意義:一是施暴人實施家庭暴力,往往是一個長期、反復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大部分家庭暴力行為,依照刑法的規定構成虐待罪,但其中又有一次或幾次家庭暴力行為,已經符合了刑法規定的故意傷害罪的構成要件,依法構成故意傷害罪。依照刑事訴訟法的規定,故意傷害罪屬于公訴案件,虐待罪沒有致被害人重傷、死亡的屬于自訴案件。人民檢察院只能對被告人犯故意傷害罪提起公訴,自訴人可以對被告人犯虐待罪另行提起告訴(即自訴)。人民法院可以將相關公訴案件和自訴案件合并審理。這樣處理,既便于在事實、證據的認定方面保持一致,也有利于全面反映被告人實施家庭暴力犯罪的多種情節,綜合衡量應當判處的刑罰,還有利于節省司法資源。本案的審判程序即反映出涉及家庭暴力犯罪案件“公訴、自訴合并審理”的特點。二是未成年子女的親生父母離婚后,對該子女的監護權都是法定的,沒有權利放棄、轉讓,不論是否和該子女共同居住,仍然屬于該子女的法定代理人。在未成年子女遭受侵害的時候,未與該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仍然可以以法定代理人的身份,代為提起告訴。本案被害人張某的生母張美麗,在與張某的生父張建志離婚后,雖然沒有與張某共同生活,但其作為張某的法定代理人,代張某向人民法院提起虐待罪告訴,是合乎法律規定的。







